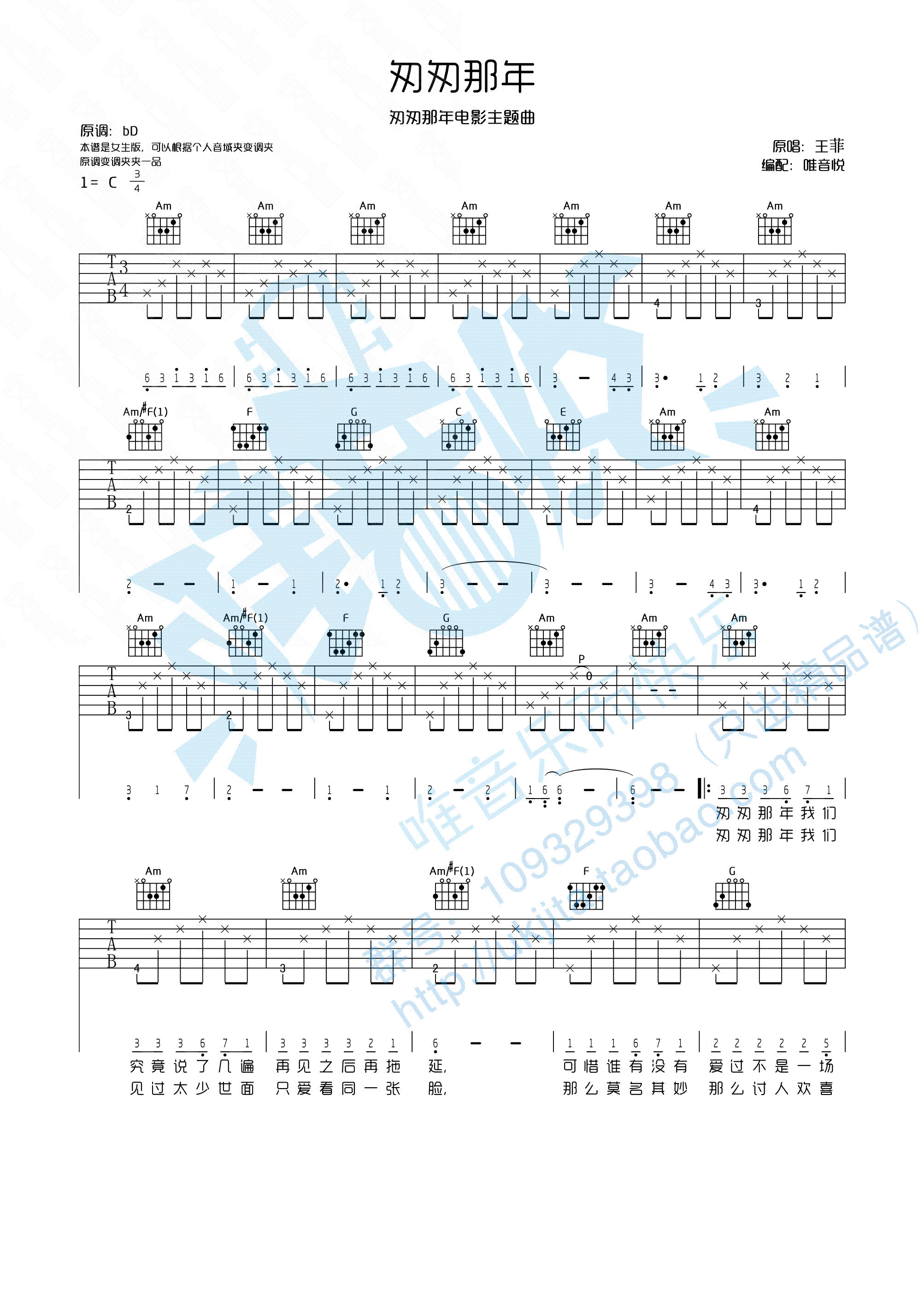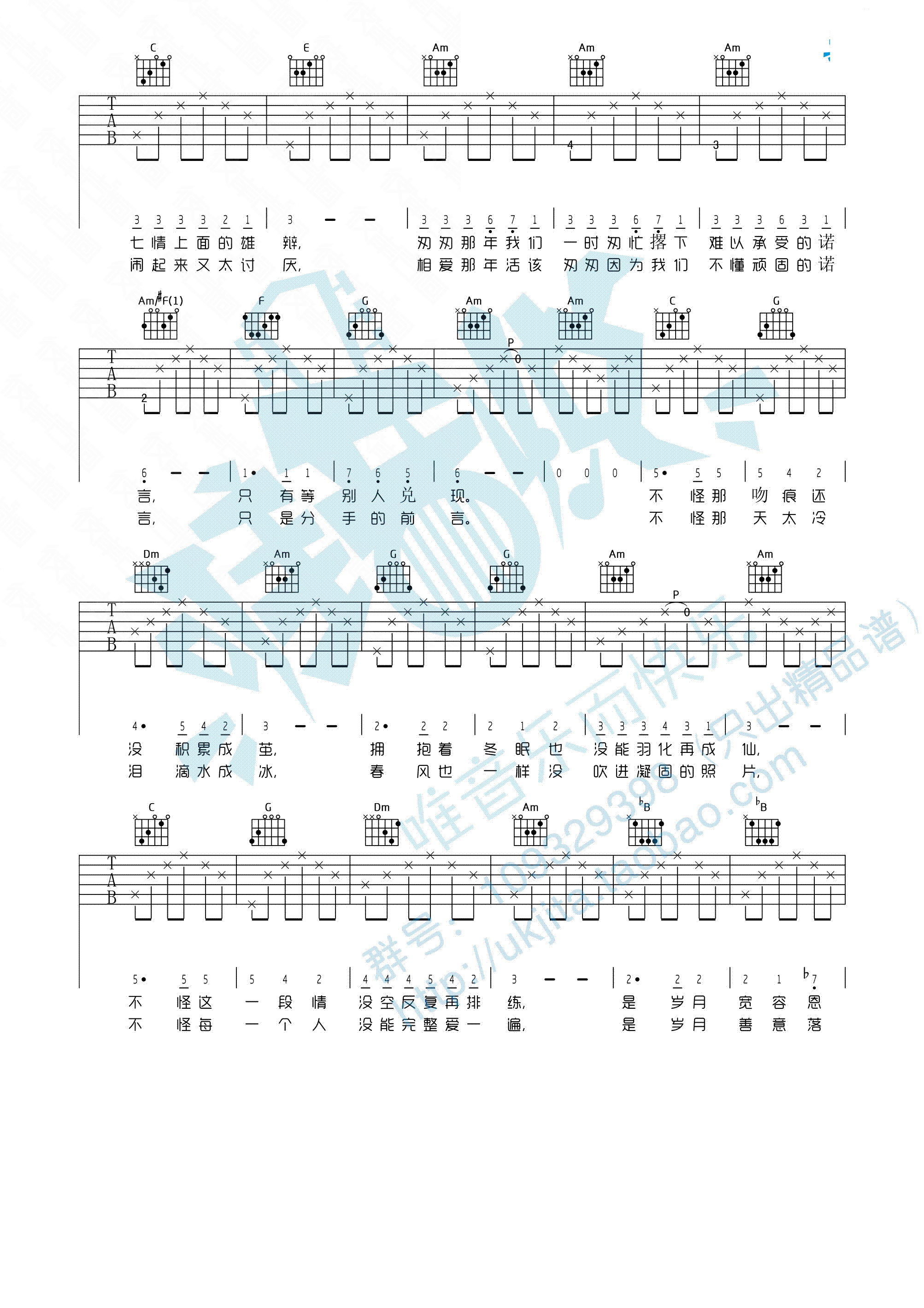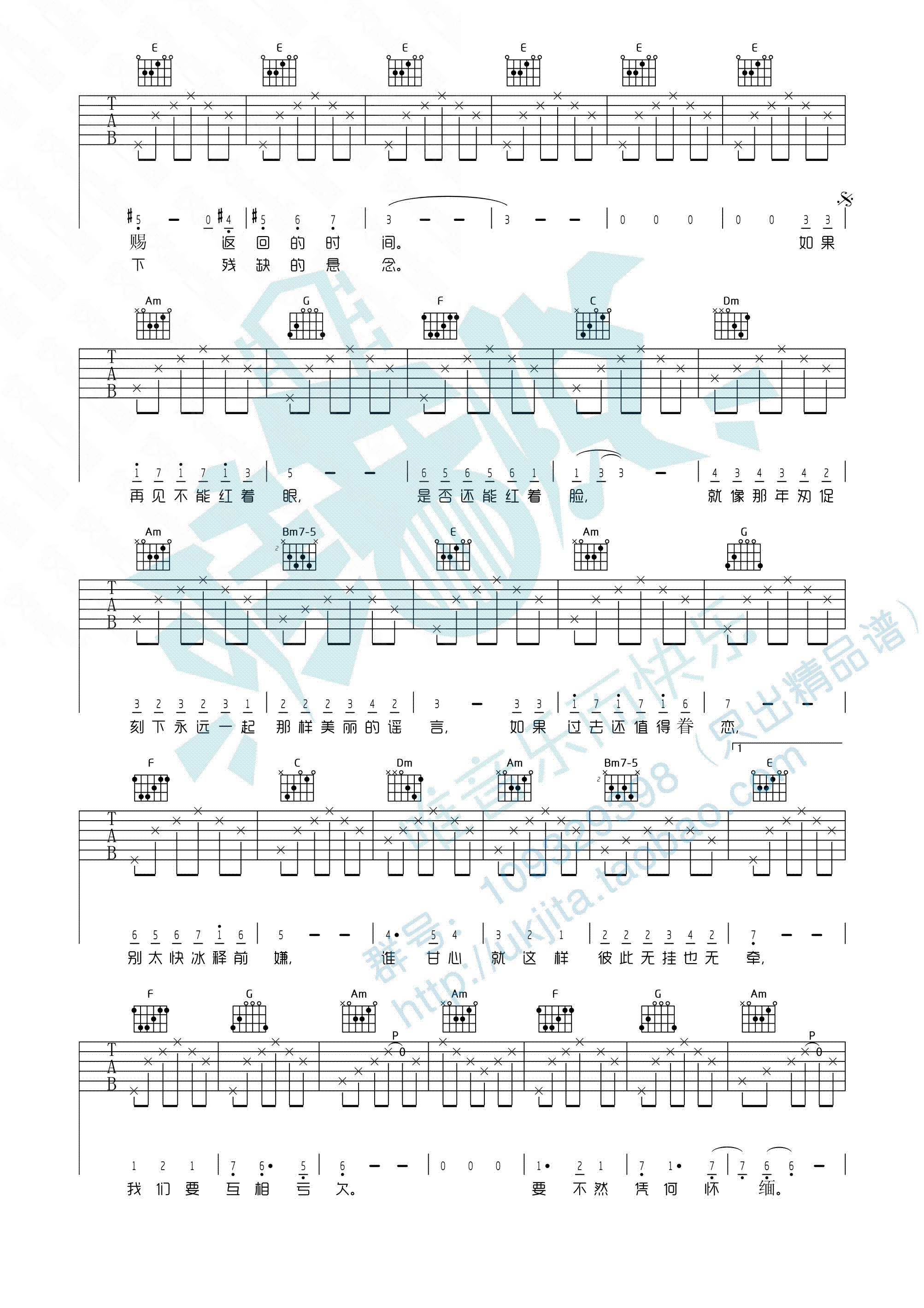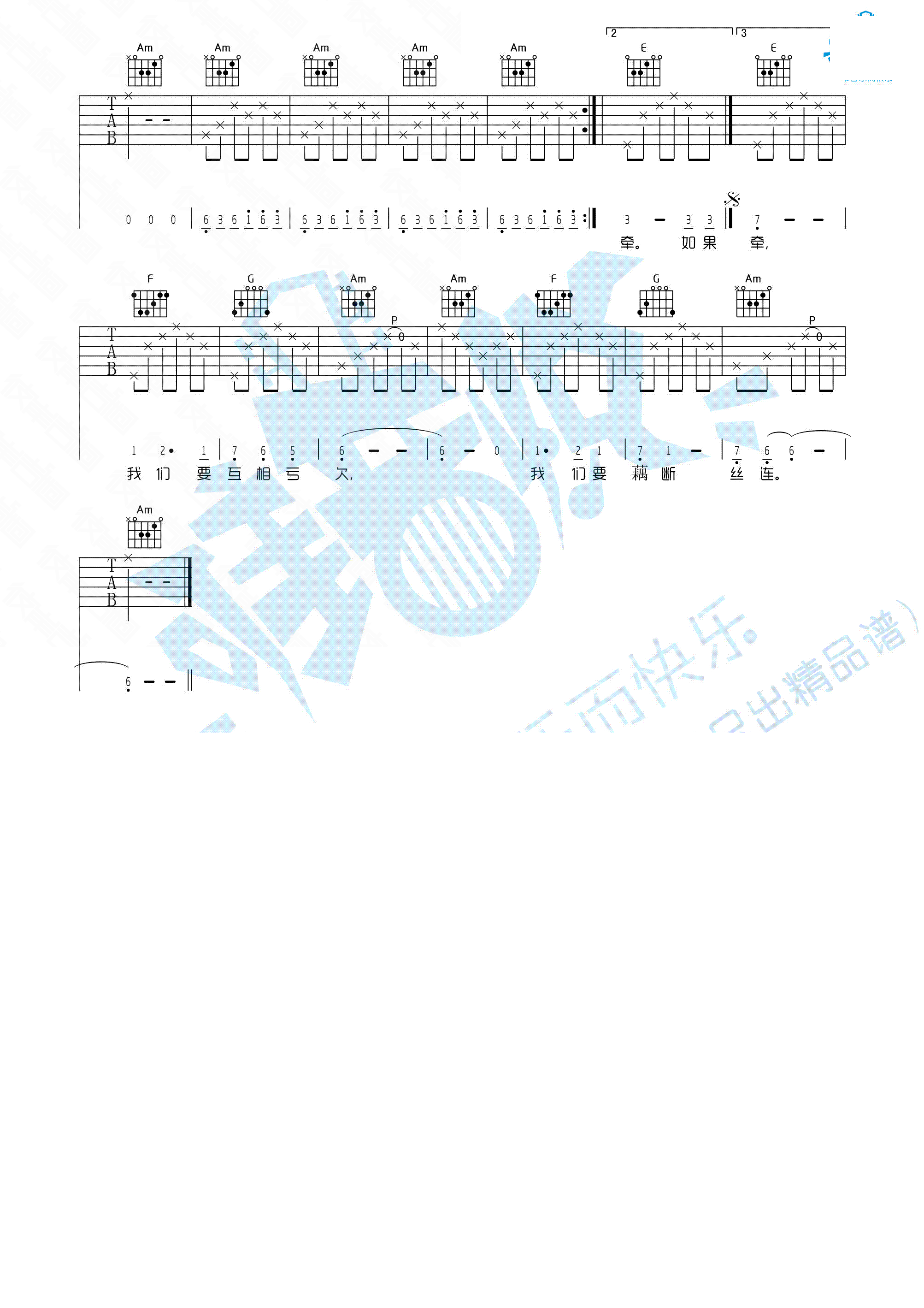《匆匆那年》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青春记忆的易逝与珍贵,通过四季轮回的意象串联起年少情感的脉络。歌词中“梧桐树下”“单车后座”等具象场景承载着集体青春记忆的符号,将个人体验升华为一代人的情感共鸣。时间在歌词中被具象为“偷走青丝”的窃贼,与“刻在桌角的誓言”形成锋利对比,暗喻成长中纯真消逝的必然性。副歌部分反复出现的“匆匆”二字形成听觉锤击,强化了岁月流逝的急促感,而“那年”的时空定格又构建出记忆的琥珀效应,使遗憾与美好在词句中达成微妙平衡。歌词中“未寄出的信纸”“半块橡皮”等细节物件成为情感载体,体现东方美学中“见微知著”的抒情传统。在情感表达上既保持“发乎情止乎礼”的含蓄,又通过“灼伤眼眶”等身体隐喻实现情感的爆破式释放。整首作品构成多声部的青春咏叹,既有对懵懂爱恋的温柔回望,也包含对时间暴力的诗意抵抗,最终在“风干成书签”的意象中完成对逝水年华的审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