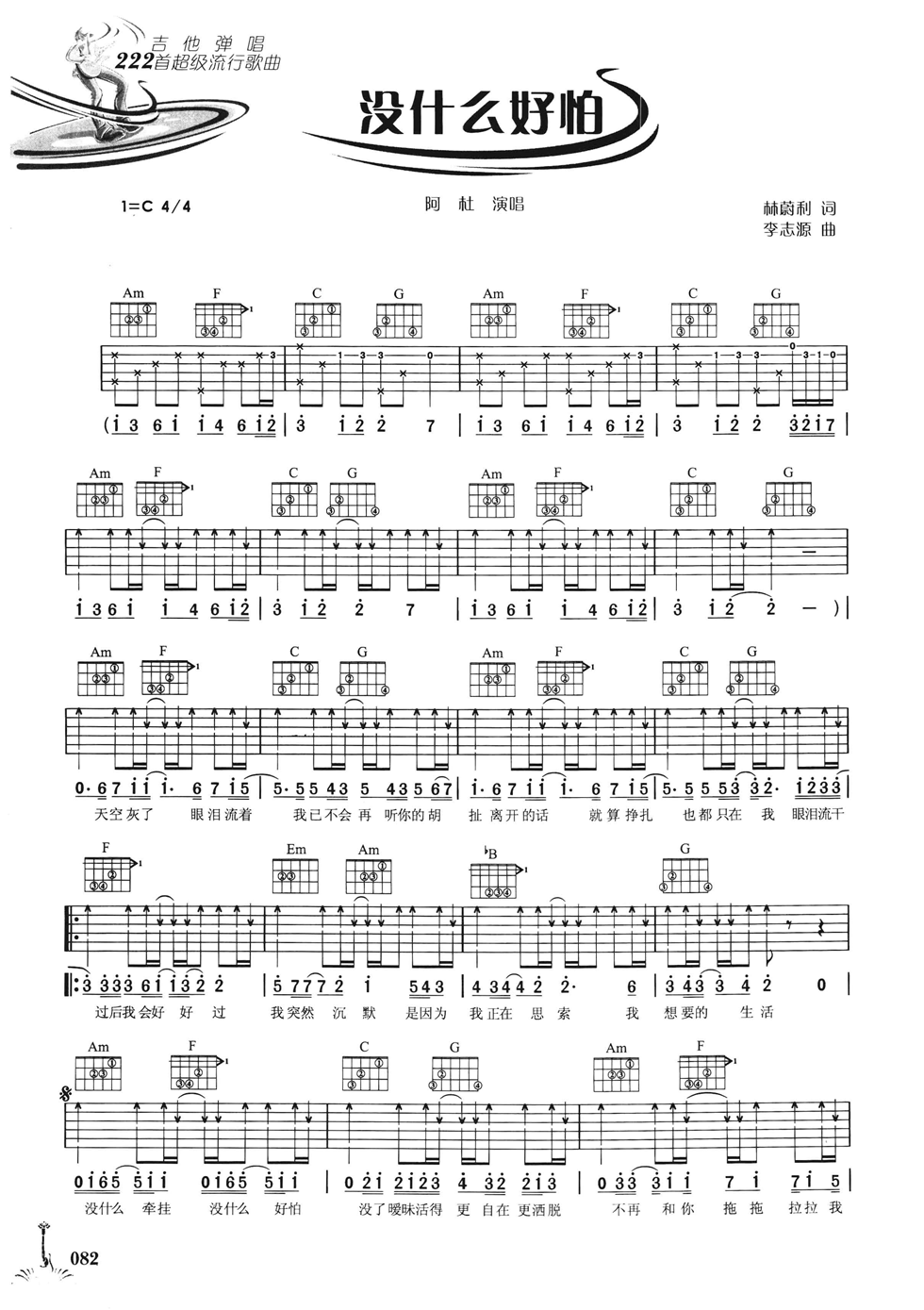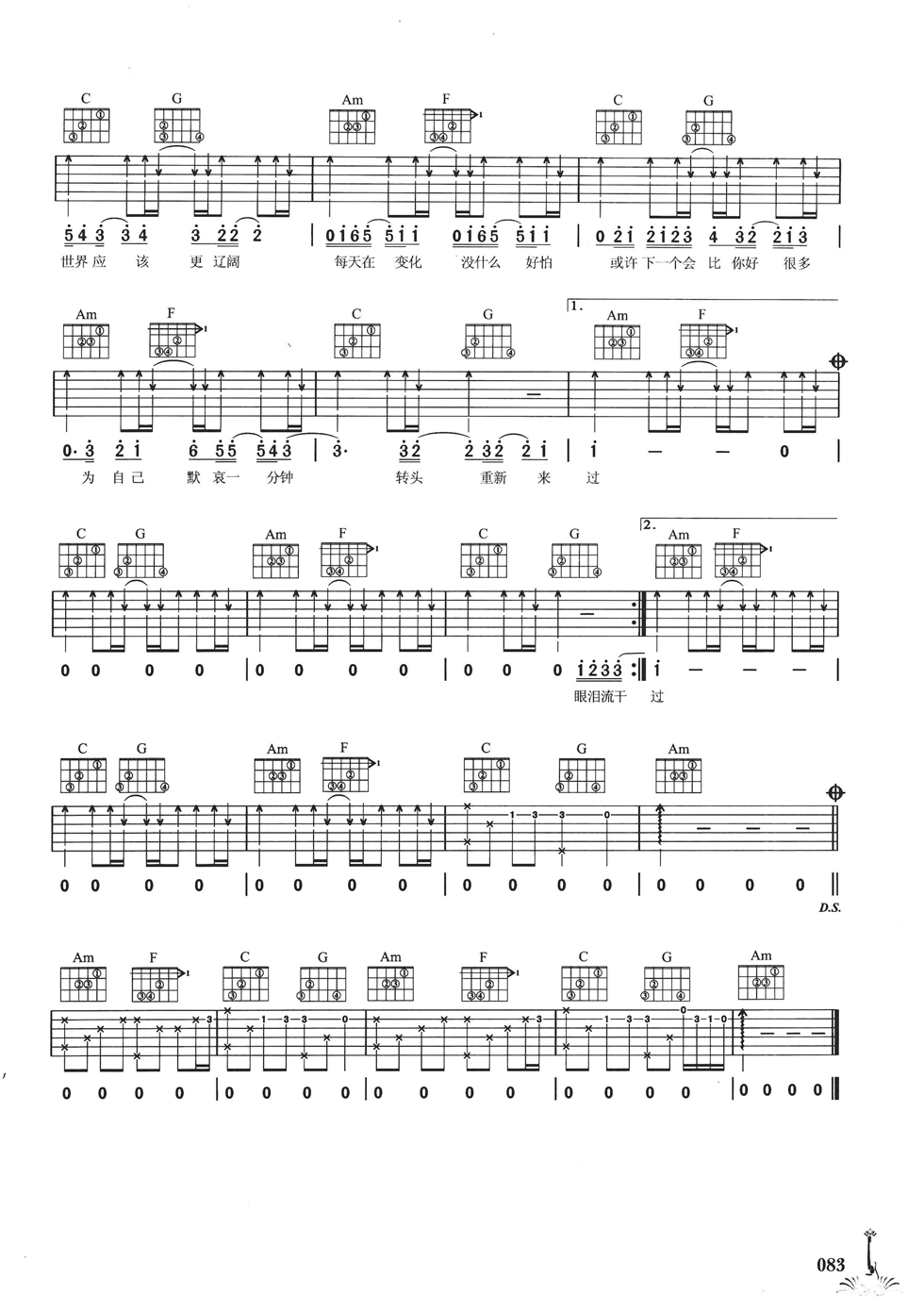《没什么好怕》以直白有力的文字拆解恐惧的虚妄本质,将人生困境具象为暴风雨、悬崖、黑夜等自然意象,却在反复吟唱的副歌中完成对恐惧的解构。歌词采用对抗性叙事结构,前半段罗列具象恐惧场景,后半段以“不过”为转折点,揭示所有恐惧终将“碎成渣”的必然结局,形成情绪上的张力反转。核心意象“伤疤”被赋予双重象征意义,既是过往痛苦的烙印,亦是生命韧性的勋章,这种辩证思维贯穿全篇。歌词刻意规避抽象说教,用“拳头握紧”“咬碎牙”等身体性动作强调对抗的实感,通过“暴雨再大浇不灭火花”等超现实主义比喻,展现原始生命力的不可摧毁性。在韵律设计上,短句与长句交替形成呼吸感,大量爆破音的使用制造出语言层面的战斗节奏,使文本本身成为对抗恐惧的武器。最终传达出存在主义式的生存态度:恐惧并非用于克服的障碍,而是淬炼生命强度的必需元素,当个体选择直视深渊时,深渊亦在重塑个体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