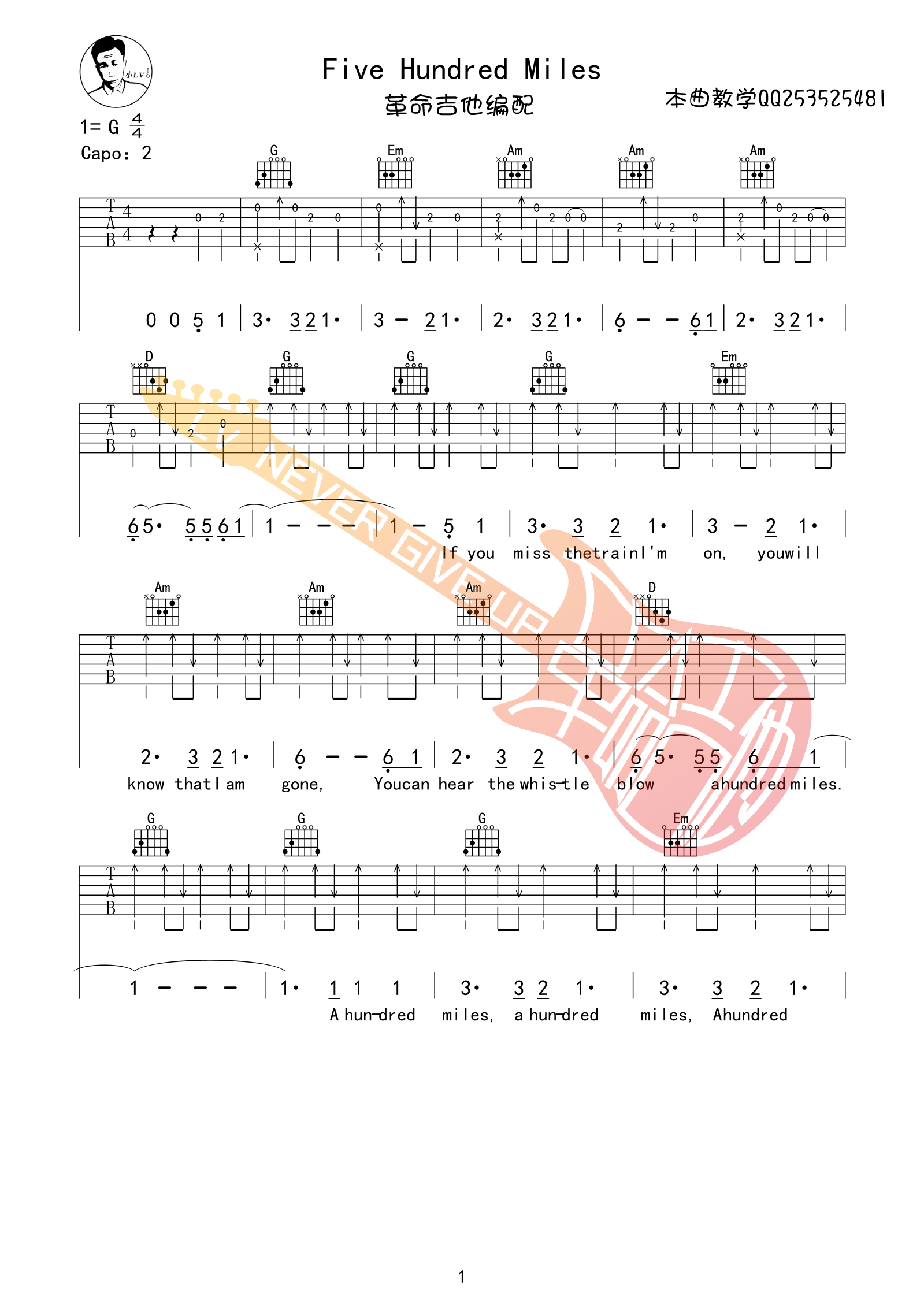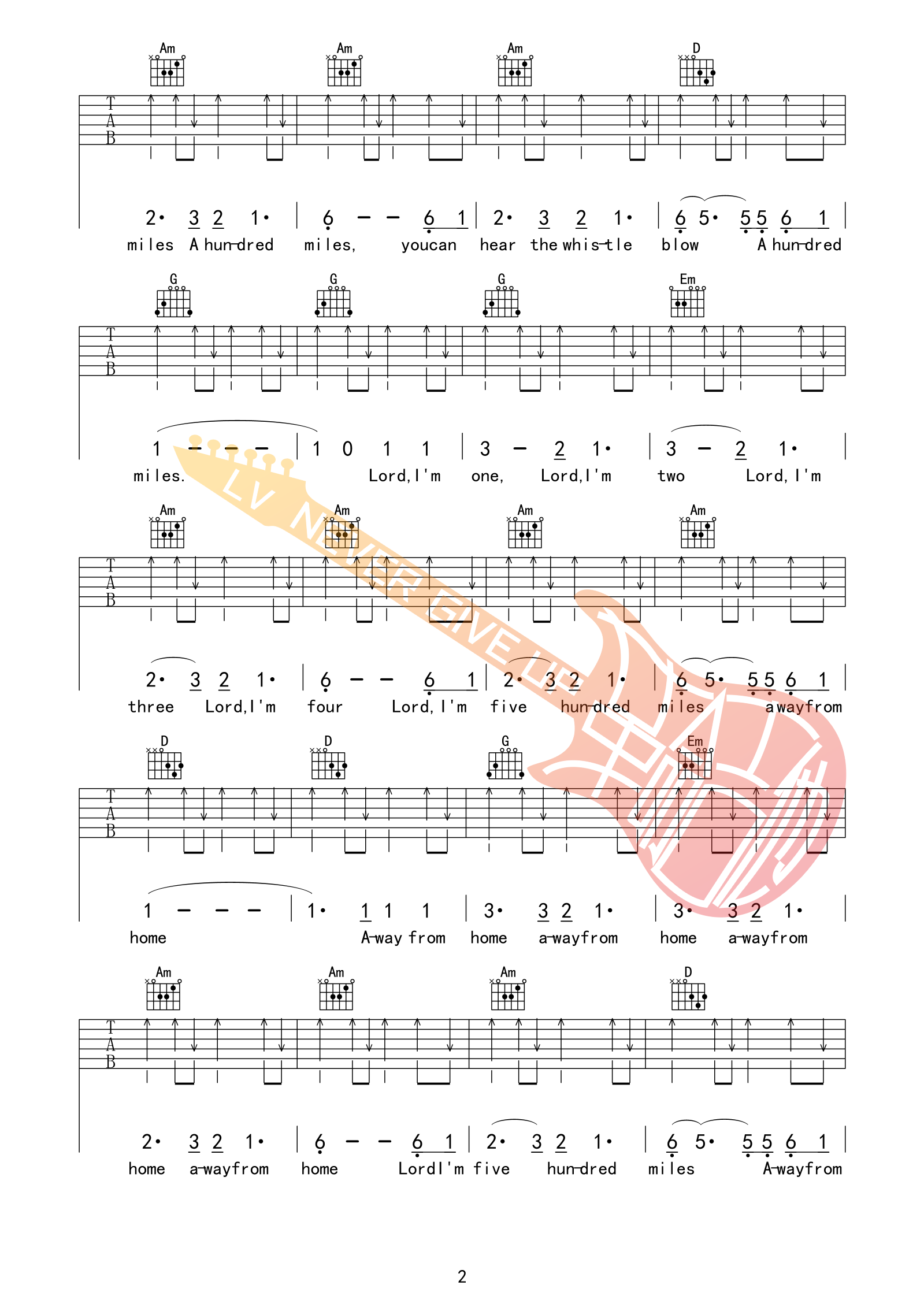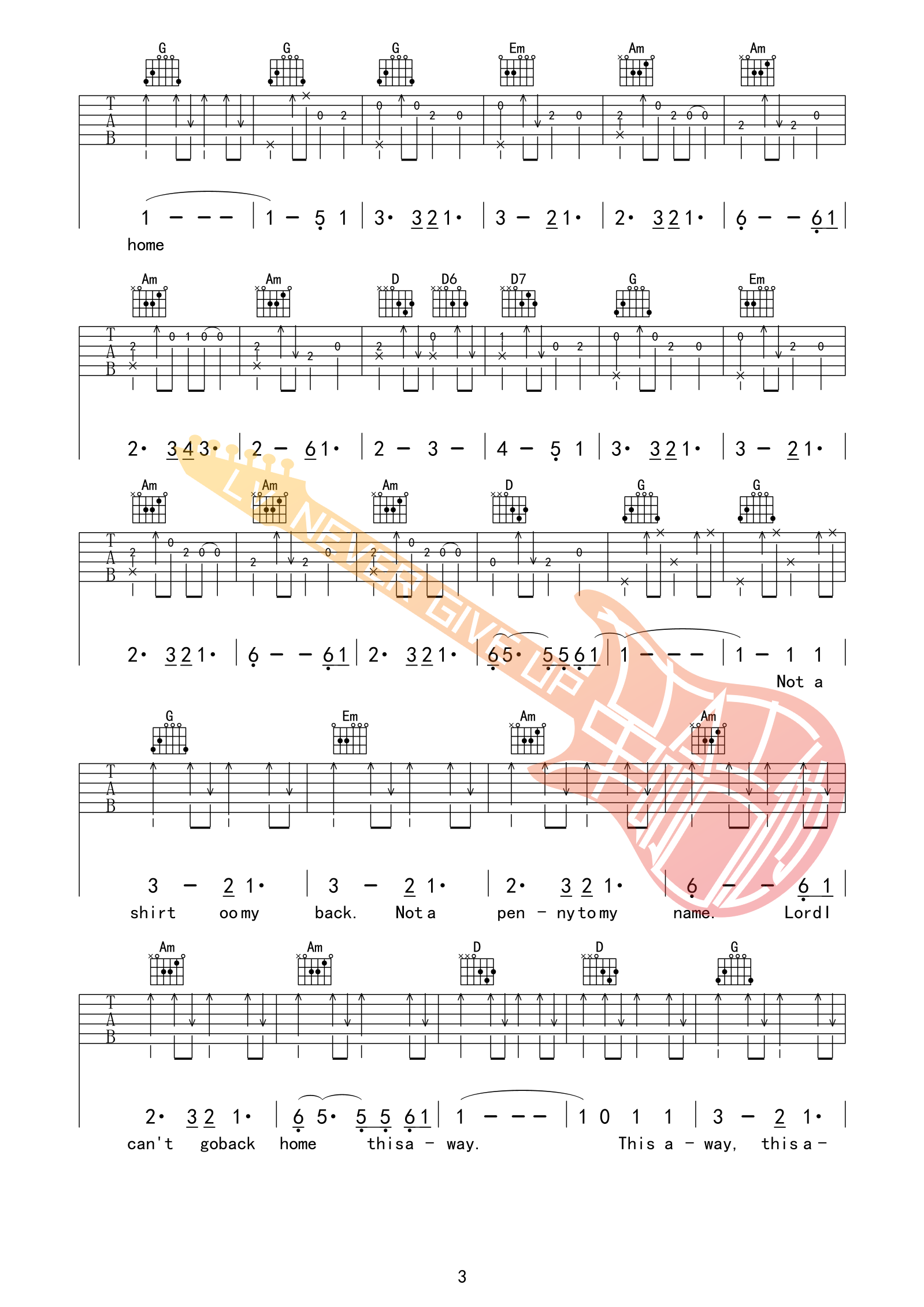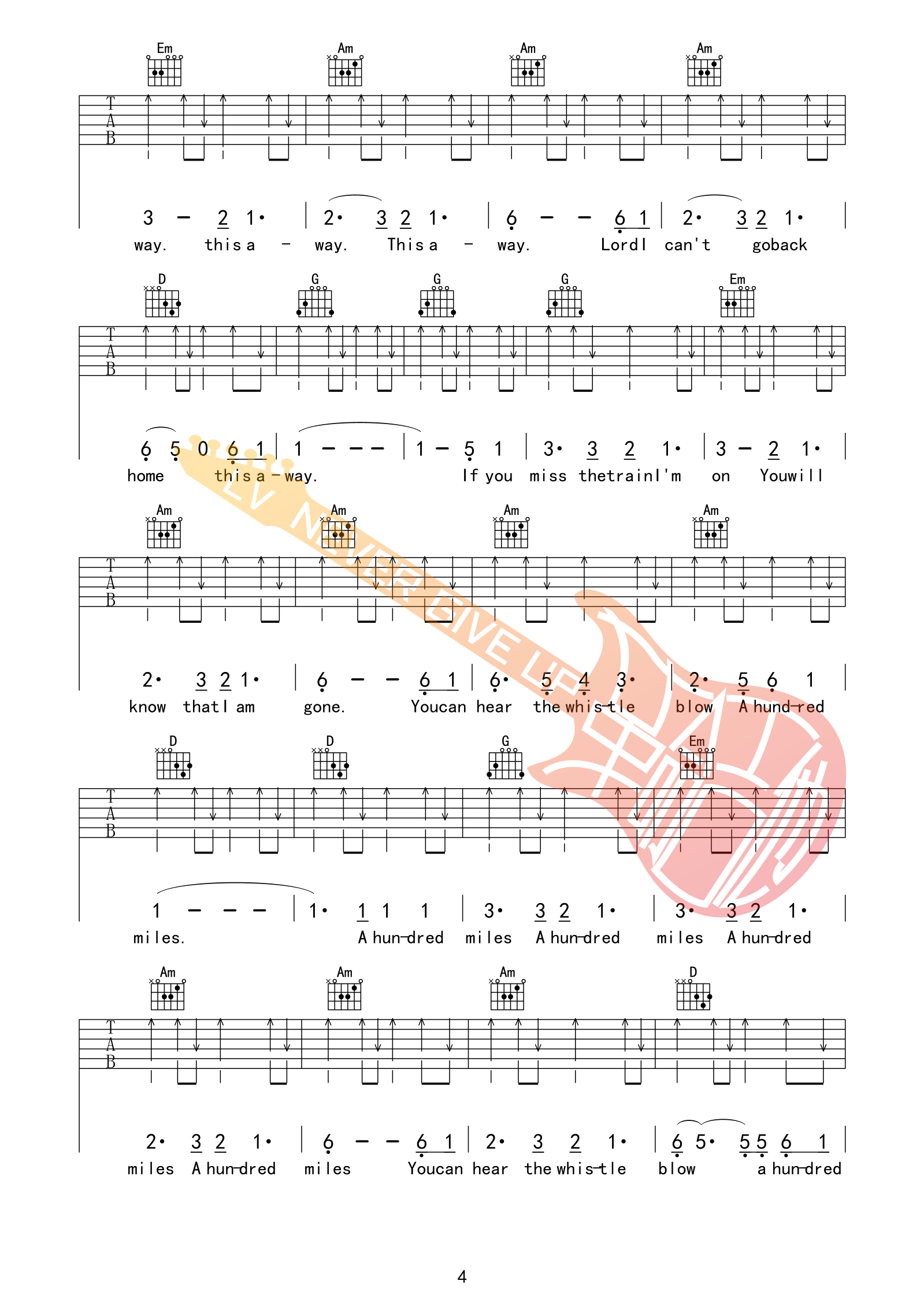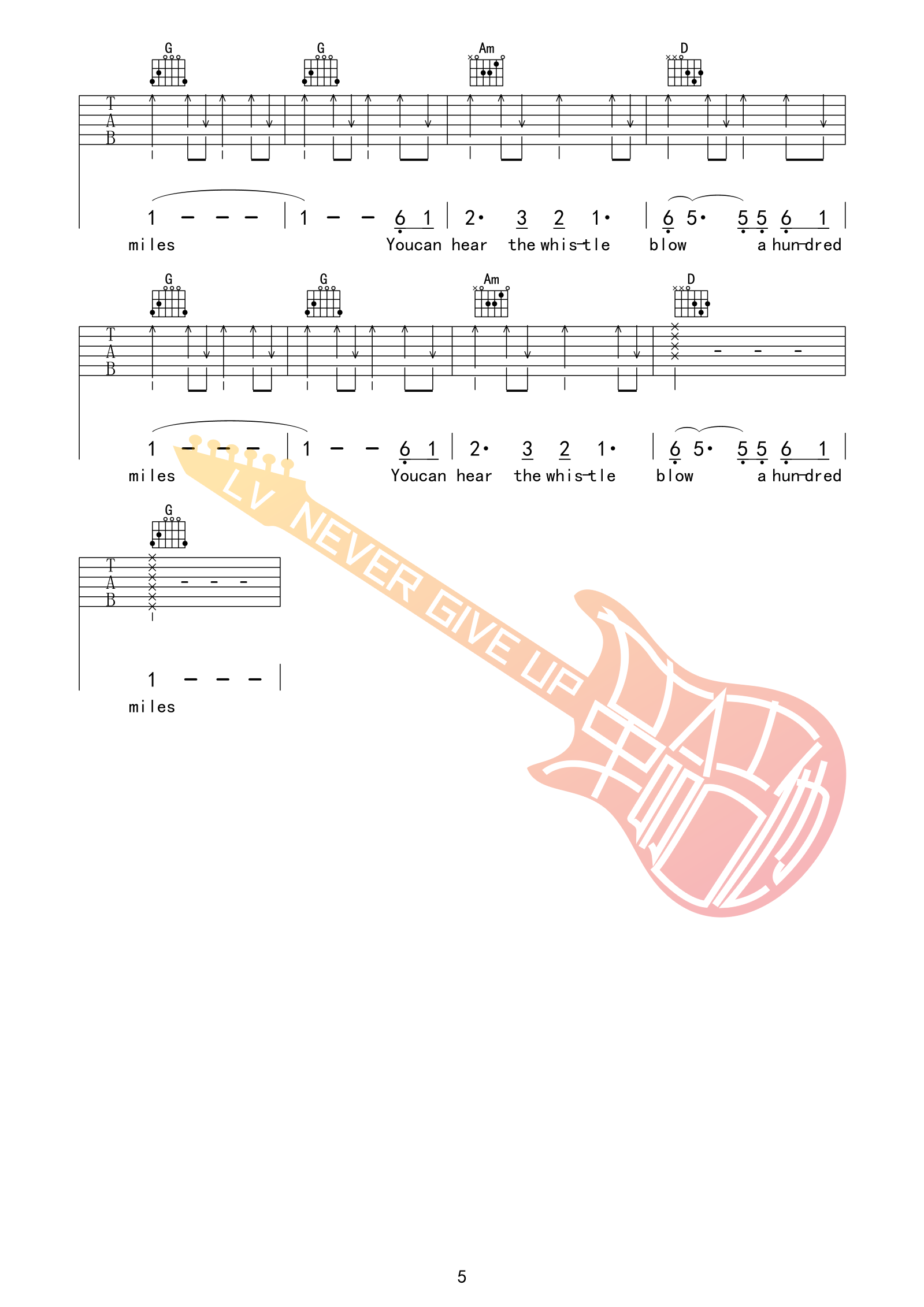《Five hundred miles》以平实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漂泊者与故乡渐行渐远的画面,字里行间渗透着乡愁与无奈。歌词中重复出现的“五百英里”不仅是物理距离的累积,更象征了游子与故土之间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铁路意象贯穿全曲,车轮声与汽笛声仿佛命运的节拍器,敲打着离人无法回头的宿命感。衣衫褴褛、身无分文的描写并非单纯的物质困境,而是揭示出漂泊者尊严与归属感的双重失落——这种穷困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荒芜。歌词中“不能归去”的哀叹并非不愿,实属不能,暗示了现实生活的重压与承诺未竟的愧疚交织成的无形枷锁。烟囱中飘散的蒸汽既是工业时代的具象符号,也隐喻着乡愁如烟般萦绕不散却抓握不住的特性。整首作品通过极简的叙事结构,将个体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迁徙之痛,让每个聆听者都能在旋律中照见自己生命中那些无法折返的远方与始终眺望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