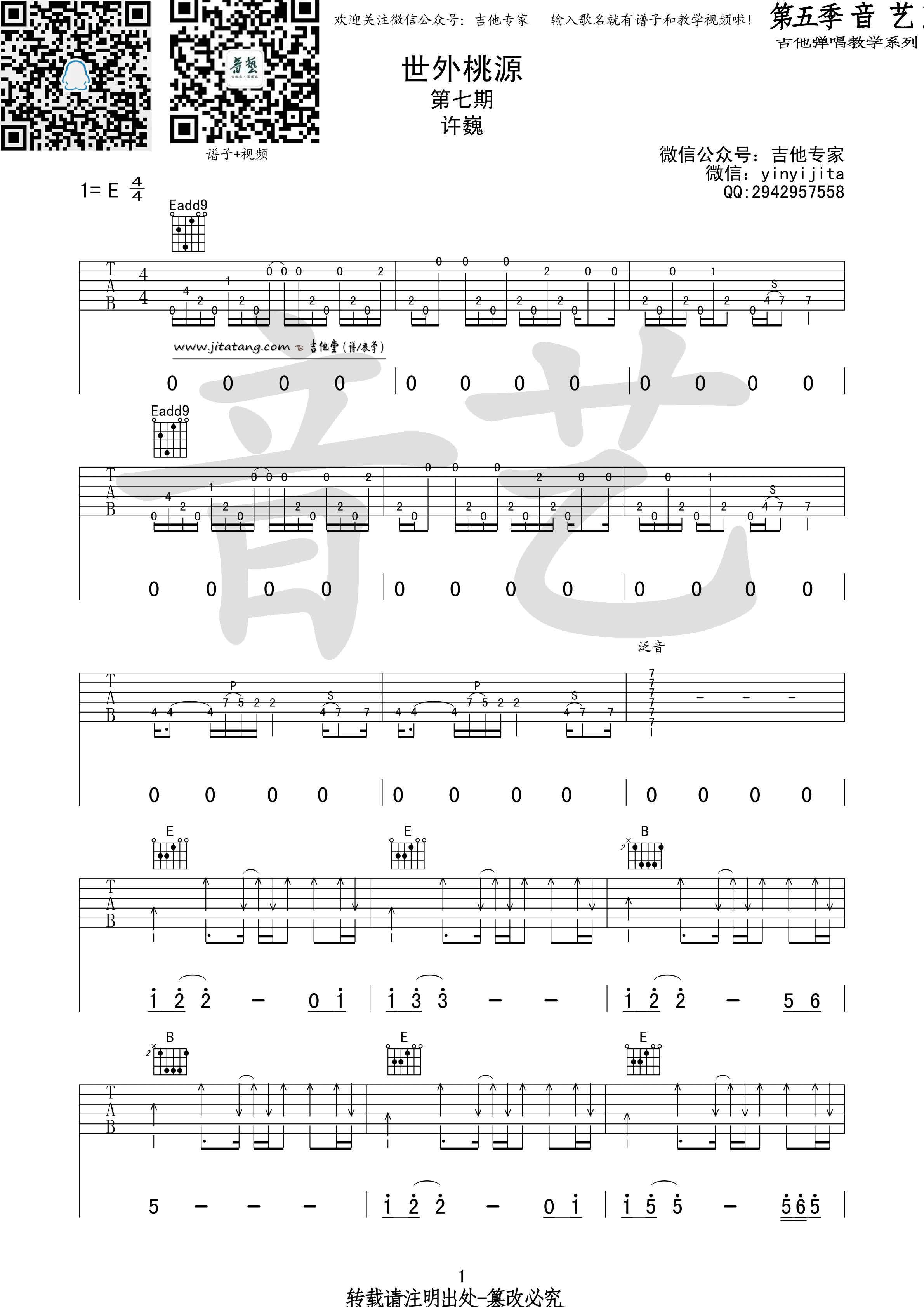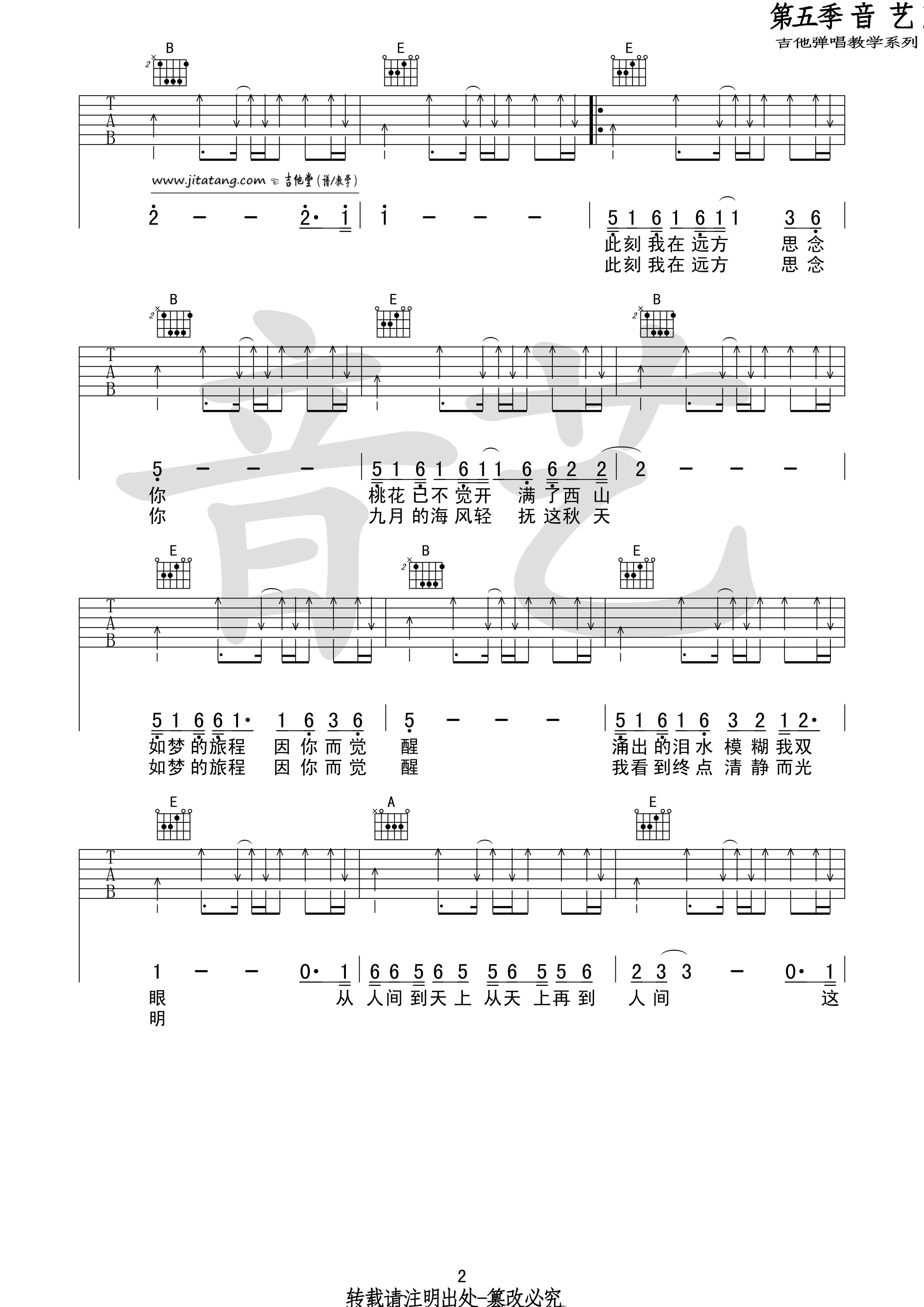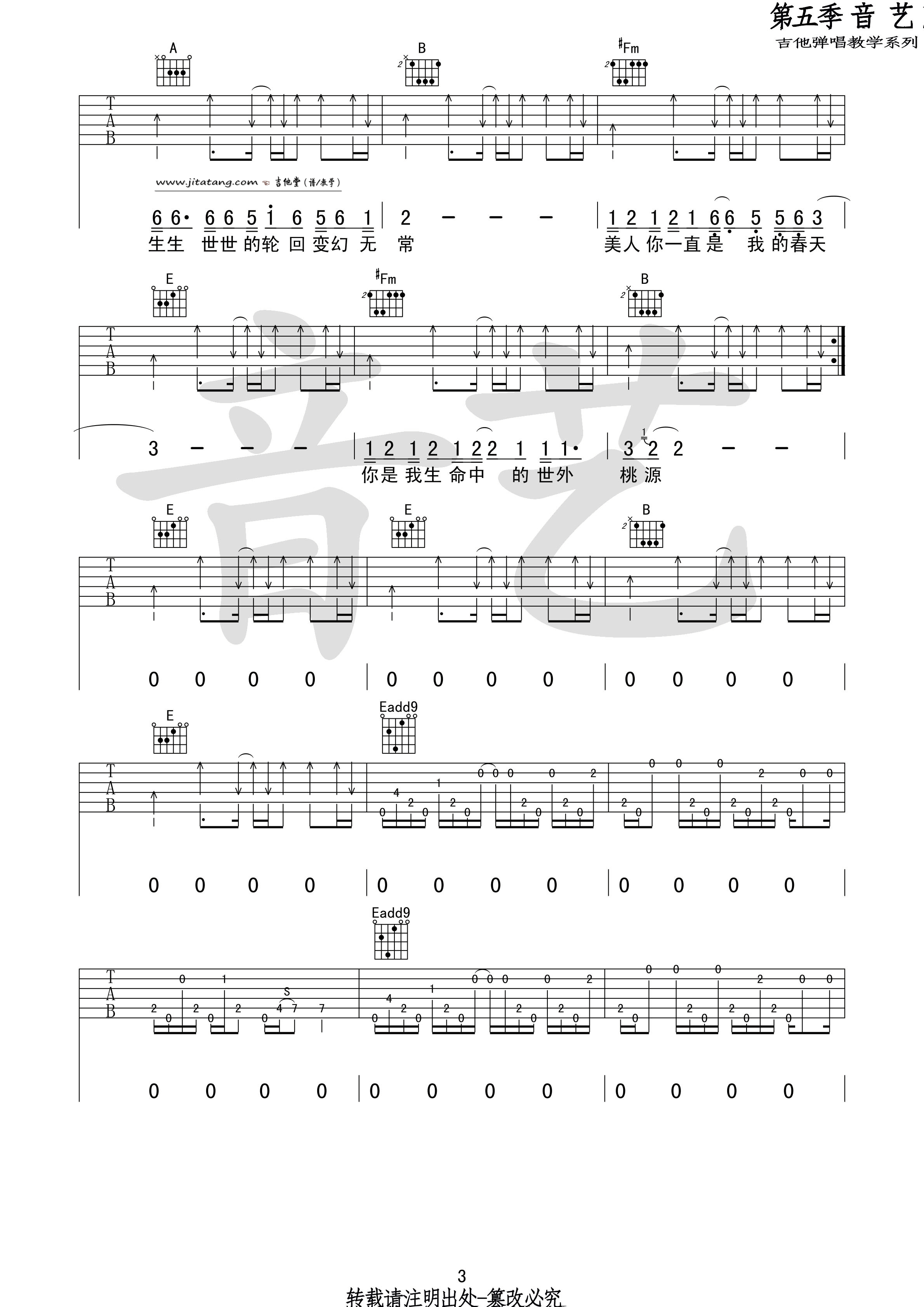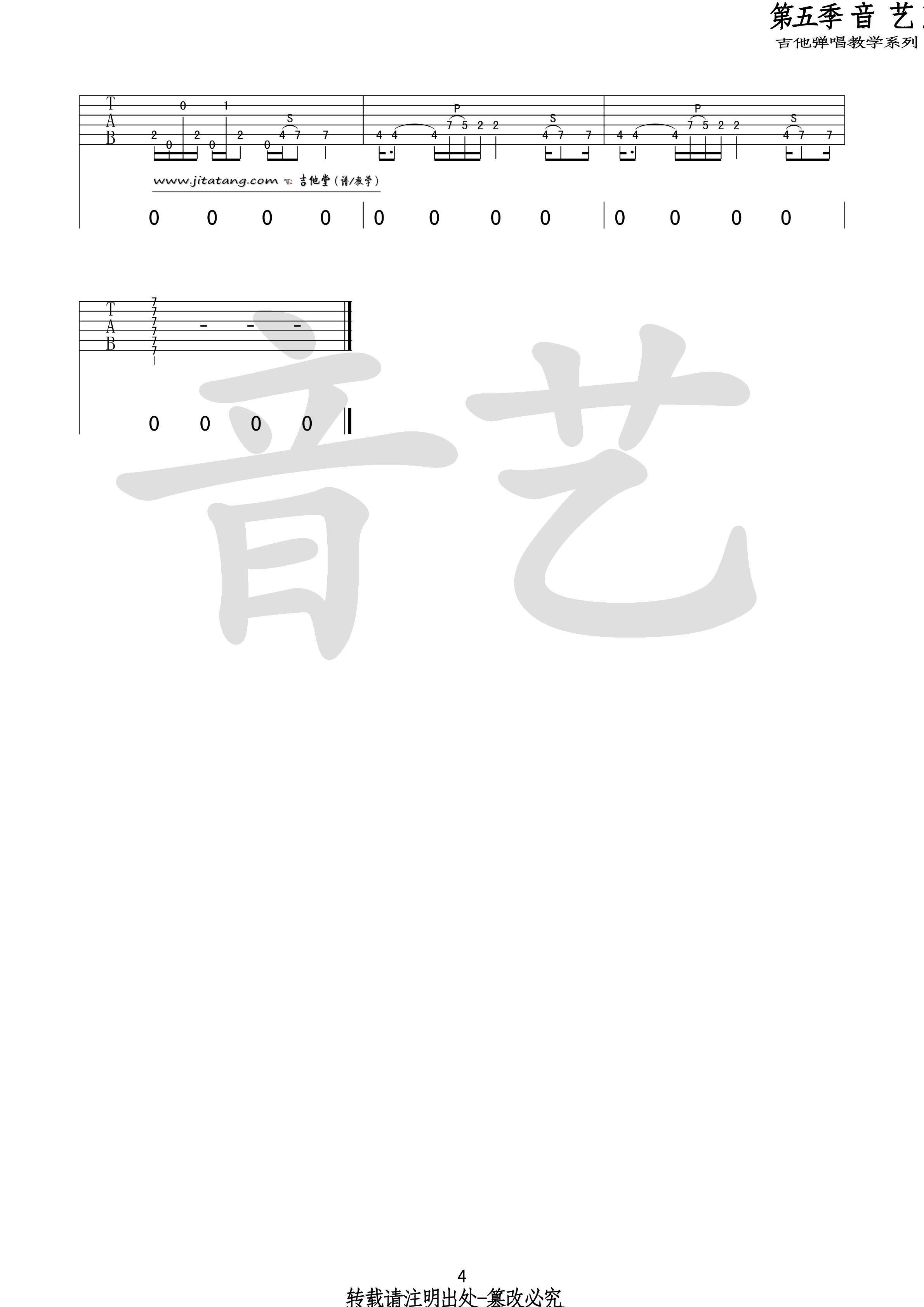《世外桃源》以隐喻笔触构建虚实交织的精神栖息地,通过溪水、桃林、薄雾等意象群勾勒出超脱尘嚣的理想之境。歌词表层描绘自然静谧之美,深层暗喻现代人对心灵原乡的永恒追寻,渔舟唱晚与柴门犬吠的田园画面,实为对抗城市异化的精神解毒剂。月光穿林与落花浮水的动态意象,暗示永恒与瞬息的哲学思辨,而"无岁月之标记"的表述直指当代人渴望逃离线性时间压迫的集体潜意识。副歌部分重复的"归途"意象形成强烈情感张力,既指向地理意义上的故土,更隐喻生命本真的回归路径。创作将陶渊明式的古典乌托邦想象进行当代转译,山外烽火与桃源安宁的对比,暗合后工业时代物质丰沛与精神荒芜的悖论。最终未完成的寻找过程本身,恰恰揭示理想主义在现实语境中的存在方式——非实体化的目的地,而是永恒跋涉的姿态。全篇以含蓄的东方美学语言,完成对物质主义浪潮的温柔抵抗,让听众在旋律间隙窥见灵魂深处未曾泯灭的星光。